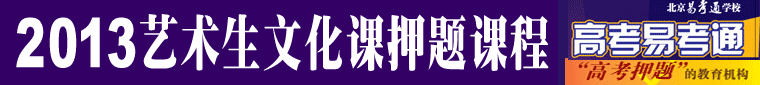高校扩招十年录取率达60%招生及就业受争议(二)
时间:2010-09-01 来源:《小康》杂志 录入:ms211中国美术高考网
网络自学会成为未来大学的新模式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预言说,5年以后,学生们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刹车失灵的电车正冲向轨道前方的五个工人,作为司机,你如果不改变行驶方向,那么五人必死。此时,有一条分叉轨道可供你转弯,不过分叉轨道上也站着一个工人。拯救直行道上的五个人将以牺牲分叉道上的一个人为代价,你会如何选择?”
2010年,一个电车撞人的公开课视频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开来。故事出自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开设的政治哲学课“正义”(Justice)。偶然看到这堂课的网络视频时,英语专业的王翔说他想不出该驶向哪边,“但正因为纠结,所以一下子就被这门课粘住了。”
王翔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道德争论,于是翻译之后,他把带有中文字幕的视频传到了互联网上。只是那时他还不知,一些著名的字幕组早就开始成规模地为中国网友译介类似课程。
几个月后,被粘住的已不止王翔一个人,粘住人们的也不止“正义”这一门课——耶鲁、剑桥、斯坦福的教授们,用英语和桑德尔般引人入胜的方法,解读西方历史、人类学或狭义相对论。如此高端、易得、妙趣横生的教育资源,不受青睐也难,特别是在当下人人标榜学习的时代。
网上的“百家讲坛”
情理之中,对于这样的视频,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但几乎所有人在看过之后都觉得应该早点了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们认为这些课程绝对值得体验,而那些理由,大多就来自对比。
王翔说,他也曾看过国内一些大学的课程视频,“好不好我无法评论,但感觉限制太多,而且我知道XX大学说过,要把一些言论不当的教师清出课堂。”
王翔说这话的8月中旬,由若干位当代著名学者主讲的通识教育课已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几天。“非常精彩!只有120个座位,但听讲的人站满了教室走廊”,特意从外地赶到北京的穆心说。魅力如斯,好学者有录音、录像的想法便是意料中事。“不过老师一再强调,录音自己学习可以,但千万不要传到网上。”穆心对此深表理解,“老师在小环境里讲话比较自由,传到网上就后果难料了,尤其是人文社科课程。”
然而这样的比较,同时也使外国大学课程作为“教育”资源的吸引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够真实。自从“人人字幕组”启动课程翻译项目以来,一直参与桑德尔“正义”课校对工作的Joanna已经“听讲无数”。她说是那些从没听过的知识给了她最初的新鲜感,不过她也怀疑当下的追逐者大多是在看热闹。“如果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就会选择了,我想这应该是个逐渐理性的过程”,Joanna说。
“人们不喜欢国内的课程大概是觉得都是陈词滥调,而非官方声音和西方世界的事物却总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和想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李志毓博士说。这样的评价,至少对一部分“好学者”来说算是中肯。
不过,外国大学公开课给人们的另一些感觉却格外真实。
在大学里学了七年法律的李凡对艺术颇有兴趣,他最初接触的课程是耶鲁大学克雷格·怀特教授的“聆听音乐”。两节课看下来,李凡说有很多收获,但更多的是感动。
“请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总是说‘那位女士’或‘这位先生’,而且他并不忌讳调侃自己。”李凡觉得,这种缩短了距离的平等感和国内老师的居高临下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的老师不见得对学生缺少尊重,但我们的文化不会允许他们用外国老师的方式表达尊重。”
在更多的人看来,最有意义的体验还是在外国课堂里接触知识的方式。
“那些老师是在和你一起领略某些东西,他们不是指挥官,而更像是学生的引渡者。”李凡说。
事实上,北欧各国早已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当下世界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教”被“学”所取代就势在必然。因为“所谓的‘教’,就是以‘有答案’为前提,由知道答案的人来教别人。”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几年前曾用欧洲人的这种见解提醒日本教育界,“所以北欧不主张‘教’,而贯彻‘要孩子们自己学’的想法。”
拜那些外国大学的公开课所赐,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夏天得以对此有所体悟。
“这次假设电车驶来的时候,你正站在桥上,而你旁边有个非常胖的人,胖到如果你把他推到桥下,他的身体可以挡住电车,从而救下五个工人,虽然这个胖人肯定会死。这时你又会如何选择?”这是桑德尔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此时他还没有提到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或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道德学说,但至少据电脑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说,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听懂那些理论学说的准备。
“哈佛课程的说理方式特别好,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引发你去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教你一些道理。”Joanna说,她由此更加排斥灌输式的教育。
中国课堂,如何分享
然而,在人们以零成本获得这些全球教育资源中的奢侈品时,他们或许还是“被灌输”了。
“波士顿公共电视台与哈佛大学联合出品。本节目由以下企业提供赞助……。联合赞助商包括……。”桑德尔“正义”课开始前的几屏字幕告诉人们,有人在为这些这些奢侈品的降价支付成本。
“本年度结束时,所有的视频录像都会出现在互联网上,免费对所有人开放。希望这门课能够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各个国家……我视此为耶鲁的光荣,更是对耶鲁资源的充分利用。当然,这也是耶鲁建立世界学术霸权计划中的一部分。”耶鲁大学保罗·布鲁姆教授在其“心理学导论”课上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免费开放背后的动机。
自从李凡发现这些公开课视频后,他说他有空就会和那些外国学生分享一下他们的课堂,“在他们花钱费力拆掉了大学围墙之后,我的视听进去了,但他们的知识也出来了。”
怀特教授在“聆听音乐”课上讲道,“今后,你们会成为古典音乐的给养者。你们,未来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会成为这一西方文化中灿烂瑰宝的保护人。”这时候,已经为自己赋予耶鲁学生角色的李凡觉得,他也被期待着完成这个使命。
于是问题浮现:在西方的课堂得以籍互联网灌输全球的时代,中国的课堂能否被分享?
其实在刚刚开始翻译外国公开课的时候,“人人字幕组”也曾经讨论过能否为中国大学的课程视频配上英文字幕,然后传到互联网上。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虽然可能只是暂时放弃。
“国内大学的一些课程,如果认真听的话你也会有所收获,不过这些课程形式比较死板,接受起来非常困难”,Joanna说。
“合作拍摄是最理想的,我们的原创剧制作组里有很多拍摄人才可以用上”, “人人字幕组”课程组负责人梁良这样憧憬,“如果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一起策划制作几套有代表性课程,然后向全球推广,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然而他们最终发现,憧憬或许只是憧憬,因为“向全球推广”这样的话,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说,即便合作拍摄的课程听上去和看起来都还不错。当Joanna不定期地到哈佛、耶鲁的网站上搜寻新视频时,她说她意识到中国的课堂也需要通过如哈佛、耶鲁一样全球来朝的平台来推广,只是中国得享全球来朝的平台在哪里,她和她的字幕组还不知道。
教娱时代的“学问”
这是个问题,但没有影响人们对课程本身的兴趣。李凡说,“聆听音乐”至少让他知道了什么是节拍、什么是旋律,以及如何欣赏《命运》和《欢乐颂》。不过他也坦言,这样的课程视频似乎与教育无关,“‘育’比‘教’更重要,但这需要真实的过程。如果你不能走入耶鲁的校园,那么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具备耶鲁精神的人。”
“我不会去听这样的音乐课程”,毕业于北京某音乐学院的周徽说,“但这类东西总的来说能够满足我的学习需求”。关于学习需求是什么,周徽的解释是:了解各类知识,而且确保获知的途径不那么外行,反感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深度,但欢迎兼收并蓄的广度。周徽觉得,在这个少有人能沉下心来探究什么的年代,她的学习需求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学习需求。
也许正是因为教育已经卷入消费社会的快餐化进程,所以翻译过那么多课程之后的梁良才会说,“课程很不错,但没有炒作的那么神,好处就是拓展视野,同时让你学到一些东西。”至于梁良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是“我的英文有了明显提高”。与那些能够“兼收并蓄”的知识相比,原来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英文才是最终的真实。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知识吗?”这是李志毓博士的问题,但她并不期待答案。“当外国大学课程视频、“TED”——一个与“科技”(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相关的演讲节目,以及“百家讲坛”等信息民主化平台使所有的知识对所有人而言都触手可及时,大量来得过于容易的也许真的会丧失“育“的意义。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表示,在5年以后,年轻人可能不用再去大学接受教育,他们只要在家打开计算机连上网络,就能轻松地获取知识,而且这些课程可能比任何一所大学提供的都还要优质。
事实上,在耶鲁、哈佛、麻省理工等美国知名高校都纷纷网上开课,放出了课堂实录的下载后,其中YOUTUBE已有300家大学的200门课程和6万堂录像课。当下中国的网络传播则有另外的渠道,电视上“百家讲坛”的火播让人窥到了中年人的知识饥渴,但是青少年们则更喜欢袁腾飞这样的另类教师,讲给他们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后者正是因网络视频的传播才“红”极一时。
当你可以自由选择,大学的门不再是唯一的通路。
一所现实大学,一所网络大学,如果教学内容都一样,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台湾教改为什么会失败
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的,但是1990年之后启动的教育改革却被亲历者们认为是台湾近年来社会发展最大的失败。台湾教改的经验或可当作“它山之石”。
文|龚鹏程
20世纪70年代,我参与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后来自己操办了两所大学,校长当了十几年,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惨痛经验和教训,今天再来回顾这样的历程,未免百感交集。
台湾教育从受称道到非改不可
1895~1945年,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当时台湾的现代教育体制是移植于日本。但实际上,台湾本地人几乎很少能够上高中,读高中后能上大学的就更少了。幸而能读的,读的也是工程、渔业,或者是少量的医科,人文社会学科是绝对没有的,所有想学人文的台湾青年只能到日本去或者想办法出国留学。这就限制了台湾高级人才的发展。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教育基础。必须在非常有限的资源下,慢慢地重新建立台湾的教育体系。1950~1970年代这二三十年间,台湾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备。1968年以后,台湾开始实施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一般评价台湾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还不错,可以说就是教育提供了相当好的、非常平均、有素质的人力资源,所以当时的台湾教育比较受称道。
但是,1980年代以后,这个本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却备受质疑。在批评和争议中慢慢开始酝酿改革。到199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运动,称为教育改革。当时曾经有过一次社会调查,问青年:你觉得我们社会哪些问题最紧迫?大家觉得最严重、排名第一的是教育。可见当时整个社会觉得,台湾教育是非改不可了!
为什么原来觉得还不错的教育,到了90年代就非改不可呢?因为,台湾号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是仰赖教育体系,对专门人才的训练促进了经济。但是正因为这样,教育是被规划的,该有多少学校、该设哪些科系,乃是根据经济计划来考虑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系的社会,却有着一个计划经济式的教育体制,你说协调不协调?教育变成了工具,大家当然会有很大的意见,人们常说台湾其实没有几十所大学,只有一所大学,就叫“教育部大学”。大学其实应该根据学校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提供不同的管理体系,但这些,当时是没有的。
此外,大学还有一个非改不可的原因:整个校园里,无论是执教者还是受教者,都不快乐,非常苦闷。因为入学很困难,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入学压力非常大,当时台湾考生都要参加恶性补习。其次是入学后,学生都是带着功利目的而来,每个人想通过教育使自己“富国强兵”,将来找到好的工作,赚钱。可是,这么读书,学生读起来会有乐趣吗?毕业以后事实上也缺乏价值感,因为读这个专业只是为了钱,所以完全不快乐。再者,整个大学类似工厂,学生类似工厂里的工人,老师类似工厂里的技师,教你娴熟工种的知识,通过测验以后送入社会。这样的大学还不该改革吗?
台湾教改的脉络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呢?当时的教育改革有几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是与台湾当时政治民主化之政治改革同步的。政治若想改革,必然先要在思想上解放,所以校园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没有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就不可能产生政治民主,故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前身就是校园的改变。
第二个脉络,是对大学本身的性质重新来做检讨。当时的教育由于要配合经济发展,以致教育功利化、工具化,所以大学里学术气氛并不浓,教授们也很少写论文。如要改革,是不是应该由教授知识的创新、研究来带动教学呢?诸如此类的讨论很多,有的是想建立大学的学术导向,有的要推行通识教育,以改造大学功利性的知识倾向。这些都是对大学性质的调整。
第三个部分,是大学内部的整体结构重组。原来大学的行政体系,校长是官派的,底下的下属都像做官一样。所以就有许多人提出大学校长要有遴选制度,要有任期制;大学内部各级的人员由学校自选;关于学生的权利义务、老师的权利义务等也该重新拟定。这是大学校园内部重整的问题。当然也跟政治退出校园有关。
最后,新教育的模式被提了出来。新教育的模式,是要打破现状的。通识教育就有这样的意向,所谓通识教育,目的并不是在大学里增加一点东西,而是要颠覆现有的专业教育体制。但是大学里很难做到这一点。台湾当时是从小学做起,有强调人本教育的森林小学、毛毛虫小学等等。森林小学,在山里面办。学生不参加义务教育式的教学,是家长和老师合作办一种新模式的学校。
各种方向不断在尝试,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就汇聚成一个大的气候,几百个社团集体上街游行,逼使“行政院”成立了教改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由李远哲主导,提了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报告,主要的关键词叫做“松绑”,就是让学校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命,结构上有若干自由。
以此进行的改革,相关的内容非常多,前后大概有上百项。大原则是松绑,通过松绑也开放了私人办学。这里要补充一点,台湾私立大学很多是1949年前大陆大学在台湾设的分校,后来就暂停申办学校。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重新开放私人办学。松绑之余的另一个重点,是人本教育。我们过去的教育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职业为本,假如以人为本的话,就要发展全人教育、通识教育,或者是终身教育。
以上是台湾在教育改革上大体的方向。
教改的失败
可是,当时提的热热闹闹的教改,后来大家却基本把它当个笑话,或者说是悲剧。社会大体上认为它是失败的。
为什么失败呢?原因非常复杂。
整个教育改革不是说几句我们要以人为本、要松绑的话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松绑,私人可以办学,但是松绑是有过程的。就像我原来办的学校,申请的时候,只同意开放办工学院,所以我只能申请办南华工学院。后来开放商管学院了,才又去改为管理学院。又后来,才再开放人文和社会学院。开放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人文放在最后面,整个教育改革那么庞大,绝不是说提升了理念马上就可以改变的。
松绑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国民党还没松手呢,民进党却又插了手进来,结果是政治化愈趋严重,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减反增。学校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各政党都在学校里各自选取支点,在里面运作。做学者很困难,学者几乎都被贴上了标签,你是绿的我是蓝的,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话,选择发言角度,以利于他言论的传销。官方教改领导人李远哲的政治立场及作为,更是备受质疑。变成这样以后,愈发显得所谓的教改非常荒谬。
而且行政力量继续在做经费的介入和绩效管理。三天两头要评鉴,大学要评鉴、设施要评鉴、老师要评鉴,用这些来进行行政管理、绩效评估。经费介入更是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些种种都造成教改困难重重。
还有就是整个高校的规模扩张。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广设高中大学。希望增加学生的就学机会、降低学生压力。结果是大学的数量激增到一两百家,也鼓励大学合并,以扩大学校规模。地方政治人物竞选,想发展地方经济也往往主张增设大学,作为政治上的筹码。大学内部组织庞大,数量又多,当然就会考虑经济上的运作,因而越来越强调要引进企业管理经营模式。过去我们若批评大学是学店,是骂人的话,现在的大学却是公然做学店,且以做学店为傲。有些学校还强调老师就像店员,学生是顾客,顾客是上帝,你要好好伺候这些学生,否则学生不来读了,老师就没有薪水。弄得教师毫无尊严,士气大受打击,人人意兴阑珊。
其他原因还很多,不再赘述。总之,台湾的教改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李远哲先生等人提出的改革多半属于体制、权力分配、技术性的问题,对教育的精神内涵却讨论很少。正因为没有内涵的讨论和导引的方向,缺乏价值目标,所以教改没有未来。
当时基本上又只是处理眼前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未来。比如“广设高中大学”就是典型例子。当初为了解决学生入学困难,结果是现在大学却设得太多。大学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个学校准备招生1000人,结果只招到30个人,像这样的学校不是一所,而是很多。学生5科0分,也有学校可以读的。这样的学生到大学来,大学还不敢当掉他,已经不够人了,再当掉学生,学校就要关门了。所以,目前的困难都是因为当时没有长远的视野。
而且改革的过程变成了资源和权力重组的内部争夺。表面看起来是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校园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过去更激烈。“教育部”每年谈的是5年500亿要分给哪些学校,学校抢来抢去。大家讲的好听,大学多元化,要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社区型大学,但是谁也不愿意做社区型大学,都想做研究型大学,因为只有研究型大学才能分得到钱。所谓教授治校,教授在学校里天天不做学问了,拿着大学法规在学校里大斗法,天天开会,忙得不得了。大学的世俗化又比过去更甚,大学没有办法给社会提供价值性的发展方向,反而流行的是大众通俗文化,呈现出来的价值观是:学者想着做官,大学生则崇拜流行偶像远甚于学院里重要的学术型学者。企业管理的精神又贯穿在大学制度里,整个学校都世俗化了,对现实世界价值不但没有批评,基本上是顺从的、艳羡的。
体制也没有改变。虽然大讲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学习型社会,理念上谈得很多,但仍然是专业化的体制、功利化的导向,仍然要深深嵌入市场化的机制里面去。我们的教学活动,又仍然是机械化的从记忆到考试,再到遗忘。考试完了,学生也就忘了。毕业拿到文凭以后,更是连教科书都丢了,老师是谁也不记得了。
所以,整个台湾的教育改革时间很长、规模很大,但是失败了。这不是我个人的评价,而是台湾社会的公论。内地人看台湾,可能会觉得政治上乌烟瘴气是个问题。但是在台湾,社会上常觉得我们最大的失败其实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失败使得台湾生命力斫伤了许多。
提供这样惨痛的经验和教训,给各位做参考,相信对大陆也会有不少借鉴作用。
(作者为台湾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今年5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举办的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本人审定,有删节。)
( 文章转载请标明:ms211中国美术高考网 )
- 中国画室大全_画室排名不分先后
- 北京画室排名(北京美术培训)
- 河北画室排名(河北美术培训)
- 天津画室排名(天津美术培训)
- 内蒙古画室排名(内蒙古美术培训)
- 山西画室排名(山西美术培训)
- 上海画室排名(上海美术培训)
- 江苏画室排名(江苏美术培训)
- 浙江画室排名(浙江美术培训)
- 山东画室排名(山东美术培训)
- 福建画室排名(福建美术培训)
- 湖南画室排名(湖南美术培训)
- 湖北画室排名(湖北美术培训)
- 安徽画室排名(安徽美术培训)
- 江西画室排名(江西美术培训)
- 河南画室排名(河南美术培训)
- 陕西画室排名(陕西美术培训)
- 甘肃画室排名(甘肃美术培训)
- 宁夏画室排名(宁夏美术培训)
- 青海画室排名(青海美术培训)
- 新疆画室排名(新疆美术培训)
- 四川画室排名(四川美术培训)
- 重庆画室排名(重庆美术培训)
- 云南画室排名(云南美术培训)
- 贵州画室排名(贵州美术培训)
- 黑龙江画室排名(黑龙江美术培训)
- 吉林画室排名(吉林美术培训)
- 辽宁画室排名(辽宁美术培训)
- 广东画室排名(广东美术培训)
- 广西画室排名(广西美术培训)
- 海南画室排名(海南美术培训)
以上画室排名不分先后!